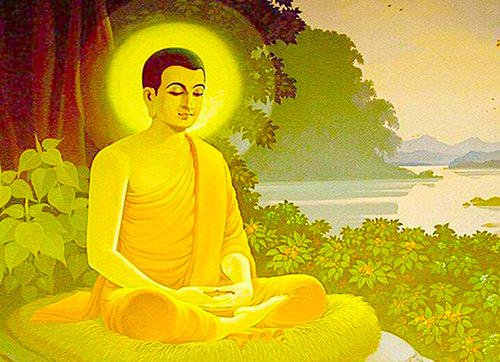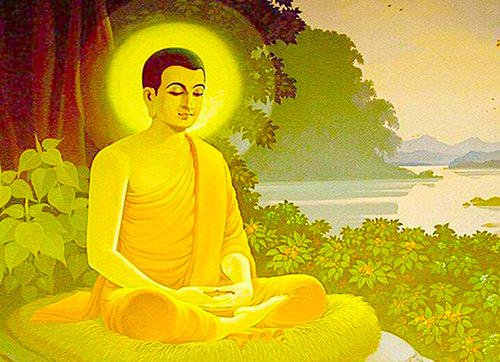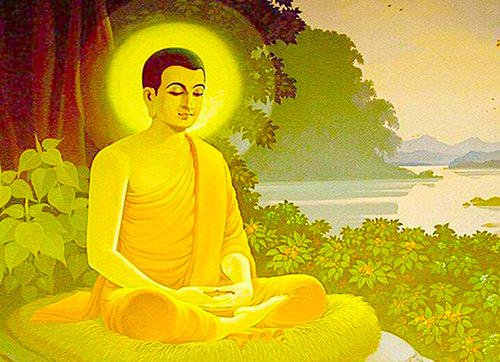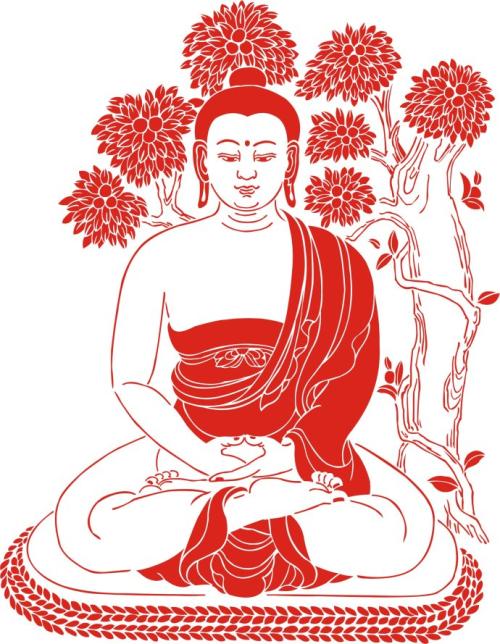唐高僧传--源流与解说
源 流
在隋唐之前,已有梁宝唱、慧皎等所编纂之十几部僧传,《梁高僧传》之「源流」部分,已对此作了介绍,今不一一赘述。道宣续慧皎之《梁传》所编纂的这部《唐传》,自问世之后,就引起了佛教界、史学界特别是佛教史界的广泛关注,不少史书都予着录,各种藏经也均有刊载。
现在较常见的线装藏经如《碛砂藏》、《嘉兴藏》、《频伽藏》及朝鲜的《高丽藏》和日本的《弘教藏》、《□字藏》、《大正藏》等均有此传,但卷数略有小异,有的为三十卷,有的为三十一卷,有的则为四十卷;所收录的人数也不尽相同,有正传三四○人、附传一六○人说,也有正传四一四人、附傅二○一人说。
为了使读者对几种卷数和收录人数不同的版本有一个梗概的了解,现对有关版本作一个简要的考察。
据着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考证:收有《唐高僧传》的大藏经,“现在通行者有三种本:一为三十卷,即高丽本及频伽本是也;二为三十一卷,即宋元本、碛砂藏本是也;三为四十卷,即嘉兴藏本及扬州本是也”。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华书局一九八八年版,第三十四页至三十五页。)此中三十卷本与三十一卷本之差异在于,后者在前者的二十卷和二十五卷后各增一卷,又把前者之二十七卷和二十八卷合为一卷,故宋元本比高丽本多出一卷;至于三十卷本与四十卷本的差异,史上说法较多:
一、《唐高僧传》作者道宣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大唐内典录》中,于《续高僧传》外,另有一《后集续高僧传》,十卷。
二、《旧唐志》中也有两部《续高僧传》之记录。
三、《开元释教录》仅载《续高僧传》三十卷,并没有《后集续高僧传》十卷。但作者智升又有:「《内典录》更有《后传》,寻本未获」之语。
陈垣根据以上资料,怀疑宋元本所增加之七十余传,即是采自《后传》,也就是说,《大唐内典录》中所说的《后集续高僧传》,后来被糅入现行之《唐高僧传》中。
至于何以由原来之三十卷,一变而为四十卷,陈先生认为主要是因为此传自《开元录略出》后,就分为四帙,而明本多以十卷为一帙,故有四十卷之说。
陈垣先生此番考证,后来得到佛教界、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在未有更多新资料足以推翻此说之前,至少可把它备为一说。
与《后集续高僧传》被糅入《唐高僧传》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几种版本所收录僧数的差异问题,对此,陈垣先生也进行了深入的考证。他认为,正因为《后集》陂糅入了《唐高僧传》,由此造成收录人数的增加,他以《唐高僧传》中实际收录的僧人,并非迄于贞观十九年,而是终于麟德二年,进一步印证了「糅入」说。
至于《后集》何时被糅入《唐高僧传》中,陈先生以慧琳《一切经音义》及可洪之《藏经音义随函录》均作三十卷,且无所增诸传之音等,说明「增多七十余传,自宋始」。
四、对于本传卷数之差异,还有一点必须于此说及,即现在流行最广的两种本子,即金陵刻经处本与《大正藏》本,它们的卷数分别为四十卷和三十卷。
我们在本书的题解中已经指出,由于金陵刻经处本几经校勘,错讹相对少些,故本书以金陵刻经处本为底本;但现在通行的各种工具书及有关资料对于《唐高僧传》卷数及其各卷与各科内容对应关系的介绍,则多持三十卷说。
为了使读者便于查阅,本书在介绍全传卷数及各卷与各科的对应关系时,取《大正藏》本的三十卷说,有鉴于此,这里有必要把金陵刻经处本和《大正藏》本各卷与各科的对应关系做一比照,使读者能一目了然:
《大正藏》本 金陵刻经处本
一、译经 第一至第四卷 第一至第五卷
二、义解 第五至第十五卷 第六王第十九卷
三、习禅 第十六至第二十卷 第二十至第二十六卷
四、明律 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二卷 第二十七至第二十九卷
五、护法 第二十三至第二十四卷 第三十至第三十二卷
六、感通 第二十五至第二十六卷 第三十三至第三十六卷
七、遗身 第二十七卷 第三十七卷
八、读诵 第二十八卷 第三十八卷
九、兴福 第二十九卷 第三十九卷
十、杂科 第三十卷 第四十卷
解 说
中国古来就有“道由人弘”的说法,意谓任何一种学说、主张乃至任何一种宗教、文化,都有赖于人的传扬、弘化。
如果说,佛教“三宝”中“法”即是指佛之“道”,那么,此中之“僧宝”就担负着弘扬「佛道」之使命,此正如元代僧人昙噩在《六学僧传?序》中所说:“佛法非僧业弗行,僧业非佛法弗明”。
可见,僧业对于佛法之传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使历史上高僧之德业能够得到表彰和弘扬,更为了时僧有所依仿、后人得到启迪,从而使佛法能够不断发扬光大,历代作者正是出于这一目的而费尽心血编纂各种《高僧传》。
自六朝至宋明各部僧传所辑录的历代高僧,或以传译经典、阐释义理而使慧灯长传,或以神通利物、遗身济众而使佛法深入人心;有的以精进修禅为四方禅林作则,有的则以戒律严谨而成为天下学僧之模范。凡此等等,历代《高僧传》确实具有“明僧业而弘佛法”之宗教意义。
其次,作为僧传,各部《高僧传》之史学价值更是勿庸置疑。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代代相续之各部《高僧传》,治中国佛教史者恐将无从下手。
不但如此,由于各部《高僧传》都是作者或花费数十年心血,甚或倾注毕生精力才完成的,他们或南走闽越、北陡燕台,或身临大川、足履危岩,碌碌奔波于荒山废剎之间,苦心搜讨于各种碑铭墓志之上,因此,僧传中所记录的许多数据,往往为正史所不载而又是研究当时许多思想家特别是佛教思想家所不可或缺的。
就此而论,各部《高僧传》不仅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进而论之,自慧皎倡高蹈远遁,易“名”以“高”,以高风亮节为选录传主之标准后,各部《高僧传》多注重僧人之道行德操,正因为如此,每个有缘读到《高僧传》的人,从书中所得到的,就不仅仅是一些佛教知识和历史资料,而是可以在思想上得到洗炼或熏陶。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僧传》还具有温渥人心、净化心灵的作用。
另外,正如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高僧传》之文化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梁》、《唐》、《宋》三部僧传中,人们看到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汇,从法显之《佛国记》到玄奘之《大唐西域记》,再到义净之《南海寄归内法传》等,都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虽然从主观上说,他们也许是为求法而西行或为弘教而求法,但在客观上,他们为中印文化之交流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再如译经,把印度佛典翻译成汉语,这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高僧传》中屡屡语及的佛经翻译之历史衍变及译经之规则,诸如道安之「五失本三不易」、隋彦琮之“八备”、唐玄奘之“五不翻”及宋赞宁之“六例”等,对于今日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当然,《高僧传》作为古代僧人的著作,一如所有的历史著作一样,都有其二重性,例如传中在赞颂高僧之道行时,往往过分渲染其神通,以至于挪动嵩岳于千里之外也易如反掌等等,
这些都有待读者加以理性的审视和甄别:又如传中虽然提供了许多甚至连正史也不曾言及的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但是,史实不当、记载错误之事亦屡屡有之,这就要求读者应该善于去伪存真、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开卷有益。